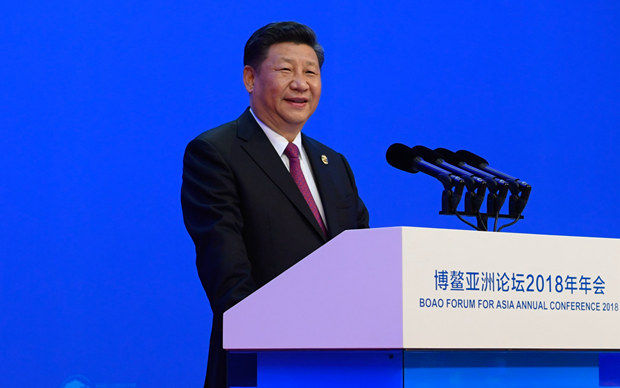雪白的浪花,随着船篙的起伏,在身后翻滚。
艄公亲切随和,一边撑篙或者划桨,一边说着一些湾里的家长里短……
(《过河回朱湖》记忆片段)
连日劳累,我不知不觉就病倒。
晚上,老爸骑着电动车,载着奄奄一息的我,到社区卫生室去打针。
上车前,他帮我把羽绒服的帽子捂上,没想到我那一辈子粗枝大叶的老爹,老了老了却变得温柔体贴了,我心中不由升腾起一股让人鼻子泛酸的暖意……
小时候,每到逢年过节,老爸就骑着二八自行车,带我们回老家。横杠上是我,后面是老妈抱着弟弟。

出城后,两边梧桐遮盖的一条小路,蜿蜒着伸向老家。
小路两旁的农田里,春有耕牛秧苗,夏闻蝉鸣荷塘,秋看金黄稻浪,冬踏白雪冰霜。
老妈嗓子亮,极喜欢唱歌,一路上,她从《一条大河》《红梅赞》《敖包相会》,又唱到《英雄赞歌》《白毛女》,再唱到《边疆的泉水清又纯》,快过河了,则是《妈妈的吻》《外婆的澎湖湾》《故乡的云》《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》……憨厚的老爸,偶尔也会跟着和几句。漫长的骑行路,似乎轻松一截了。

【台湾画家简忠威的水彩画,仅作示意】
在老妈熏陶下,我也是从小喜欢唱歌。老爸经常逗我,说我不会唱什么歌,我就不服气地唱给他听。
老弟呢,那会儿还是个白白胖胖的小憨头,啥都不懂。
老爸骑完卧龙小路的尽头,就要上府河大堤了。
堤内堤外都是成片的白杨树,站在堤顶,就可以眺望到老家的方向。
每每到这里,老爸总会唱《小白杨》,我这个麦霸,自然也是首首不落下。

【大庆油田王家彬的水粉画,仅作示意】
下了堤,过一次渡,还要步行穿越河滩,再过一次河,才能到达对岸的老家。
这也是我和弟弟最喜欢回老家的原因之一:可以坐船玩耍。
河床上的景色,也是美得不可言状。
一下堤,我和弟弟就不愿意再坐老爸的自行车了,而是在河床上撒开欢儿奔跑,躺倒在河滩的草地上打滚,从比人高的草丛间,拨开一条条冒险的新路……
尤其是清明时节,金黄的油菜花连绵成片,各种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在脚边恣意灿烂。运气好时,还能在草丛里碰到刺猬,或是野兔。几头不紧不慢得啃着嫩草的老黄牛,则时常被我和老弟撵得跑……
由于要过两次河,所以第二次过河前,躺在河滩的青草地上等船的功夫,我们也绝不闲着。采摘草丛里星星点点的紫云英,成了我和老弟的比赛项目。
臭美的我,还总爱挑两朵最好看的当耳环……

又上船了。艄公是老家大队里的乡亲。
一上船,艄公(有时又是艄婆顶班)就和老爸老妈热情打招呼、话家常。他们经常把老爸认成是我大伯或三叔(我父亲家里有兄弟四个,取名依次是“东西南北”)。
艄公亲切随和,一边撑篙或者划桨,一边说着湾里的一些闲话,如如谁家盖了新房子,谁家孩子考上了城里高中,谁家老幺在大城市找了份好工作之类的家长里短。

雪白的浪花,随着船篙的起伏,在身后翻滚。
我和弟弟就用木棍或是水草打水花玩,船舱里偶尔还有几条鱼,也不幸成了我们的玩物。
有时候,老艄公就逗我:你就是那个在城里上学、很会唱歌跳舞的小姑娘吧,那你唱歌歌爹爹听哈!
我会以此作为条件,得到撑篙玩的机会。看着比我矮小的弟弟,这时候的我,自然极其得意。

不在过年或清明节时,过河的人并不多,我们时常能遇到包船的机会。
隐约的印象中撑船的艄公,起先是位中年男子,往后的几年逐渐变成了大妈或是大爷。他们在河岸边搭一个简易草棚,河床上放着牛羊,日子慢慢的,像极了“天苍苍,野茫茫,风吹草地见牛羊”那首诗句。
两道河床间隔也不远,十分钟就能渡河。
有人在岸边喊一嗓子,艄公就应声出现。
小船除了坐人,有时还能载两三辆自行车呢。两道河间的距离隔也不算太远,十分钟就能渡一次河。

记忆中,国道通往老家的公路越来越宽,越来越好走了,村里在外工作人的,也大多有了车,回老家也就都是车去车回了。
那条要过两次河的回乡小路,已经许久没有再走过了。
而今,老爸老妈年岁也渐渐高了,再想跟他们年轻时那样,一路高歌着骑自行车由小路过河回老家,恐怕也不太现实了。
但是,老爸骑自行车的背影、老妈回荡在稻田里的歌声,那浪迹天涯的河床、水波荡漾的府河、亲切憨厚的撑篙人……仍时时萦绕在我的梦中。
我时常还惦记:那个撑篙的老爷爷,不知道还在不在呢?
原载 作者 微信号 简笔初夏

作者:简慧芳,洋湖高旗人。孝感电视台记者。